
方汉文 1950年12月出生于西安市,汉族,苏州大学比较文学研究中心主任,文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获北京师范大学文学博士学位,留美博士后。兼任北京大学、美国图兰大学、香港大学、韩国全北大学、台湾东吴大学等院校特聘教授与客座教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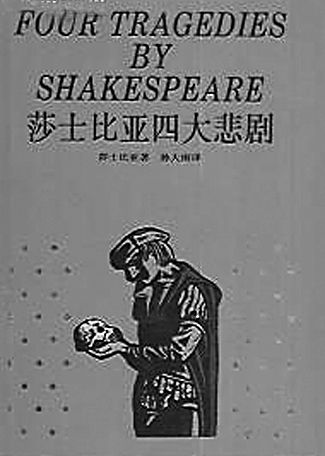
世界文学史的新建构,将东方文学纳入世界文学主体的新视域,改变传统的文学经典秩序,已经是一种学术创新。
演讲人:方汉文 时间:2012年7月18日 地点:首都经贸大学
世界文学史的新建构
21世纪初期以来,美国学术界兴起的“世界文学史新建构”(A New Construction of World Literature History, 以下简称“新建构”)是一种重要的新思潮,有学者评价为是自“理论热”之后,向世界文学史研究回归的当代学术主流之一。尤其可观的是,作为世界文学史新建构的重要实践话语──“世界文学经典选本”出现了新的趋势:中国文学(以及部分“非西方文学”)的文本以前所未有的数量与组合比例,首次与西方文学经典珠联璧合,合编在西方主要的文选之中。
美国《朗曼世界文学文选》的主编之一,“新建构”学派代表人物、哈佛大学教授达姆若什(David Damrosch)说:现在美国的世界文学课程比例中,原本的“西方传统”几乎与“非西方文学”的传统旗鼓相当。
当然,这种说法有些夸张,但是也并非完全失实,我曾经进行过粗略的统计,以诺顿、朗文的《世界文学文选》的近年版本选篇为例,入选的作品包括3000年前的西亚史诗《吉尔伽美什》到中国作家鲁迅和正在走红的日本作家村上春树,这些“非西方文学”所占的分量之大,不仅相对1650年开始出版的“诺顿文选”中的纯正的“西方传统”来说是匪夷所思的,即使就十几年前的诺顿文选的选篇而言,也是颠覆性的现象:东方文学特别是中国文学经典的成分大幅度增加。
无可怀疑,“新建构”将东方文学纳入世界文学主体的新视域,改变了传统的文学经典秩序,已经是一种学术创新。
为什么会产生这种变化?对于选编世界文学选集或是书写世界文学史的美国学者及欧洲学者而言,他们的主体想象与视域由何而来?
我们要回到2003年,这一年对于世界文学史研究是相当重要的一年,特别是对美国学者而言。哈佛大学的达姆若什这一年出版了他的代表作《什么是世界文学》,他在书中强调,西方世界文学史体现了欧美的古典与当代文学的传承固然重要,但全球化时代更需要超越“本地书籍”的“界限”,引进包括中国《诗经》在内的其他民族文化的世界文学经典,这是一种多元化的世界文学,而不是西方中心的世界文学。因为世界文学作品具有多样性,没有一个绝对统一的标准,这种文学多样性恰是全球化时代文学的根本特性之一。
其实并非他个人如此看待的,这种世界文学史观念早在赛义德等人的后殖民批评中已经孕育。也正是在2003年,美国后殖民批评家斯皮瓦克的《学科之死》出版,在这本书中还附有作者的一篇单独的论文《超越界限》。如果说《学科之死》这本书以其惊世骇俗的书名令人震撼,那么在这篇论文中,斯皮瓦克的一句名言可能对世界文学史更具有理论上的颠覆性:
在(比较)文学领域,我们需要离开“盎格鲁声腔”、“卢梭声腔”、“条顿声腔”、“法兰克声腔”等,我们必须应用南半球的语言作为有生命力的文化媒介,而不仅仅将它们作为文化研究的对象。
“盎格鲁声腔”等四个“声腔”,是指欧洲的主要民族文化与语言体系,是西方文学的代表,公元11到13世纪西欧各国开始使用自己的口语语言,官方的拉丁语名存实亡,最早出现的语言体系之一就是法兰克人的语言,到公元13至16世纪,莎士比亚与法语的《罗兰之歌》等名著已经使这些语言取代拉丁文,成为西方文学具有代表性的“声腔”。所谓“南半球”是一个泛指与象征,这包括大洋洲的土著、拉丁美洲的印第安原著民与非洲特别是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部落与民族的语言文化,这是被认为“黑暗的心脏”(康拉德语)或是“原始文化”的“第三世界”文学的声腔,斯皮瓦克恰恰要将其作为一种“有生命力的媒介”,认证这样的话语作为世界文学史的主体地位。她肯定这些被压抑的“非西方话语,就是让这些文学发出世界性的“声腔”,“声腔”这个词原义是指一种语言的单音发音,在当代批评中用来指称一种民族语言为主体的文学。
达姆若什以不同的方式表达了相近的意见,他认为在美国的“世界文学史”教学中,“超越欧洲的课程数量剧增是更为巨大的挑战,包括原典文献的亚述文、中文、日文、吉库尤文,纳瓦特尔语、盖楚瓦语、斯瓦希里语、越南语、祖鲁语和其他多种语言的作品。”
达姆洛什这段话中所涉及到语言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不再使用的古代语言,如亚述语,这是公元前1800年前后亚述王国沙姆希亚达德一世起,到公元前612年亚述王国亡于新巴比伦与米底人之间主要使用的一种语言,这种语言用泥板书写,成为亚述的研究对象。另外一类是正在使用的语言中也包括一些使用范围有限的土著部落语言如肯尼亚的吉库尤文、南非的盖楚瓦语与拉美的纳瓦特尔语,或其他使用较少的语言。达姆若什在这里以这些语言代表各自的文化体系。
他说:“翻译正在成为新的纠纷事项,社会文本和文化传统在课程中问题大增,不再只关注于普通的西方传统之内的言谈的进化”。
我们认为,形成于21世纪,包括中国学者在内的“世界文学史新建构”是世界文学史研究的一次成功转型,其意义正在逐步显现出来。在西方的传统中,中国与东方文学不过是“东方学”的构成,无论是“东亚研究”或是其他地域研究,都是西方世界文学史的“他人”,这里面有一种隐含的“地域文学”的歧视与不平等。经过这种“世界文学史的新建构”,中国与其他“非西方”文学走进了世界文学史,被赋予与西方平等的“身份”的初步认证。这里的中国文学是世界文学史的一种整体性构成,这也意味着,西方为唯一主体的“世界文学史”从此要改变“独白”,要成为多声腔的合鸣。这种转型包括世界文学史的认识论、本体论、发展观,特别是它的经典选编,“世界文学史”正在发生巨变,从希腊“荷马史诗”到莎士比亚、乔伊斯的单线叙事,变换成从《吉尔伽美什》、《诗经》、《罗摩衍那》到《一千零一夜》、鲁迅、马尔克斯的多元话语。这是世界文学史书写主体性的重要改变,是对西方中心的反思后所形成的新型世界文学史。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