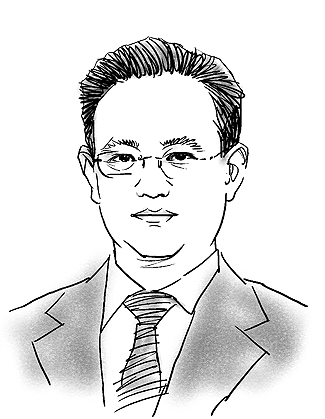
冷戰結束后20年來,民主一直是國際政治中的熱門話題。憑借對民主話語的壟斷,西方戰略家將其包裝成全人類的所謂“普世價值”和全球性政治標准。民主被西方政治理論家提煉成政治制度的唯一真諦,演變為一種政治宗教,成為西方對外輸出的政治聖經、基本軟件和影響他國的“利器”,成為打造西方霸權的“開路先鋒”。
其一,民主被泛國際化。在西方戰略家眼裡,民主已經是一種全球化現象,民主政治和自由市場一樣,成為無處不在、無所不能的價值、觀念、標准、制度、原則,甚至做法。近些年來,國際上的“民主陣營”甚為囂張,極盡政治滲透和武力干涉之能事,這不僅導致了國際關系緊張和國際政治動蕩,也延緩了一些地區政治發展的進程,敗壞了民主的聲譽,導致了以下伴生性政治“后遺症”:民主道路迷失、民主思想嬗變、民主結果異化、民主機體潰瘍、民主泛化與民主赤字並存、不少國家政治風險上升和政局動蕩頻繁。與此同時,依附性民主、復仇政治、寡頭式民主、財閥的自由等一些民主異質現象也開始出現。
其二,民主被神聖化、宗教化。在西方,民主被“教化”,主要表現為宗教化、教條化。譬如,宣揚民主拜物教,將民主形式神聖化、民主制度西式化、西式民主理論教條化、西式民主程式化和模式化。在一些西方政客眼裡,一個政治人物、一個政黨、一個國家一旦籠罩上“民主、自由”的光環,便可以隨意指責對手是野蠻的、專制的、獨裁的。對於民主的宗教化色彩及背后的戰略考慮,西方政治學者常常開門見山,毫不掩飾。比如,亨廷頓在《第三波:二十世紀末的民主化浪潮》一書中就寫道,現代民主是西方文明的產物,它扎根於西方社會﹔民主為西方所特有,可以被西方對外政策制定者所利用。
其三,民主被工具化、功利化。典型的西方政治邏輯就是:我即民主,誰不與我站在一起,誰就是民主的敵人。冷戰后,一些國家繼續以民主劃線,將世界分割成敵我對立陣營。在民主工具化和功利化的背景下,嚴肅的民主話題變成了“政治快餐”,不僅惡化了民主形象,而且引發政治沖突,誤導了一些國家對政治發展的探索,拖累了整個世界的政治發展進程。有人誤認為實行民主就是政治放鬆、絕對自由、黨派競爭,民主化就意味著要進行大規模的政治改組、政黨斗爭、投票選舉、全民公投等等。實際上,民主要求良好的政治素養和成熟的政治文化,也意味著一定程度的妥協、協商。
其四,民主被標簽化、碎片化。一些國家的政治勢力往往將民主制度與西方的政治制度簡單等同,將民主化視為西化﹔一些國家急欲給自己貼上“民主化”的標簽,以求在國際關系中能夠與“冷戰”后的西方大國站在一起﹔而一些西方國家也習慣以自己的民主框架來衡量和談論別國的政治制度或政治進程,把持民主的定義和標准,隨意給他國打上“民主”或“獨裁”的標簽。西方篤信民主的普適性和通用性,忽視民主的多樣性、現實性和發展的階段性。殊不知,民主是一個成長的過程,民主的發展程度與其所處的歷史階段密切相關。實際上,近年來包括原蘇聯、東歐地區以及拉美和非洲等國家在內,人為移植西方民主模式很少給這些地區帶來真正的民主、自由、平等和幸福。
其五,民主被程序化、格式化。這方面突出表現在將復雜龐大的政治體系簡化為民主化,並將民主化等同於選舉和多黨競爭,進而將復雜的政治民主進程簡單化為一套選舉程序。事實上,雖然選舉是必要的,是民主的重要表現和形式,但它並非民主的全部和實質。我們看到,在一些國家和地區,普選常常變成一場全社會范圍的“政治大賭博”,公民投票就像是在下“賭注”,為了贏得選舉,一些黨派和政治領袖往往不吝許諾,讓普通選民在政治制度、社會發展方向等問題上進行選擇。結果是,過分關注投票過程和結果,而忽視選舉之后的政治規制和監督制衡,造成一些政權出現憲政危機或獨裁當道,從而陷入無休止的政治動蕩和社會泥潭。在這種情況下,倘使法制軟弱無力,買賣選票和政治腐敗現象就會極為猖獗,民主就變成選票的市場交易,議會所體現的不過是院外活動集團的利益。
其六,民主被絕對化、終極化。主要表現是宣揚西式民主模式的全球普適性和歷史永恆性,認為在一國政治中,民主涵蓋了所有政治進程。在這種思想的主導下,民主成為政治發展總體進程中唯一的和終極的追求,為了追求最大限度的和絕對的“民主”,可以不顧甚至拋棄穩定、效率、秩序等政治價值。典型的例子是,蘇聯解體、東歐劇變后,在這些極度追求“民主”“自由”的國家裡就曾出現過所謂民主化浪潮。然而,這些國家的民主化潮流始終起起落落、來去匆匆,以至於短短數年時間裡,這裡的人民由“渴望民主”變為“厭倦民主”,轉而追求穩定和秩序。
|



